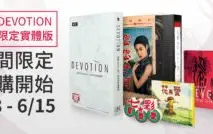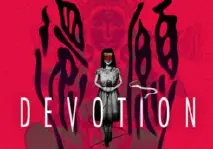先不论 Centaur 要怎样支撑威盛那“开辟新战场,延续高成长”的战略大计,光从 2000 年到 2004 年,那让人摸不着头绪的纷乱产品时程表,就够笔者和潜在客户伤透脑筋了。
回顾上篇:台湾处理器拾遗》成为威盛电子 x86 处理器技术基础的 Centaur(上)
2000 年到 2004 年的时程表大风吹
笔者不敢斩钉截铁的确信,当初威盛花大钱,一口气购入 Cyrix 和 Centaur,有没有打算建构“高低档搭配”产品线(高阶 Cyrix,中低阶 Centaur)的野心,或者觉得这两间的文化是互补的。但情势的演变,让 Centaur 不得不面对“追求高效能”的挑战──即使初代超纯量管线的 C5X,死在 Centaur 自己的手里。
砸了超过两亿美元进军 x86 处理器市场的威盛,透过收购 Cyrix 而得到的 Intel P6 总线授权,期限只到 2006 年 5 月,2001 年 3 月 25 日让 VIA C3 取代 Cyrix III,更等于直接把 Cyrix 品牌丢到水里。到头来,手上还有专利可和 Intel 讨价还价的 Centaur,乍看之下,是仅剩的有价值资产。
来自威盛高层的期望,都充分反映在“产品代号充满圣经味”的产品路线图,“双重产品代号(威盛的圣经人名和 Centaur 的 CxX)”也是威盛 x86 处理器的一大特色。更糟的是,这两者还不是“一对一”的,让产品代号与行销名称之间的对应关系,更显得混乱不堪。
眼见为凭,就请各位看倌慢慢欣赏。
2000 年:Centaur 的首要之务是持续改进并缩小 C5 家族,并追逐 1GHz 时脉。此时简报挂出来的品牌还叫做 VIA Cyrix。
此外,威盛在 2000 年 4 月 11 日以 3.23 亿美元的代价,将 S3 绘图芯片部门转移至新成立的 VIA-S3 合资公司,冒出个打包威盛北桥芯片组和 S3 绘图核心的 Matthew,实乃理所当然之事。最起码,在当时威盛高层应认定这是市场渴望的“马太福音”。

但 Centaur 有个更艰钜的任务:在越来越炽烈的效能军备竞赛,不能再像过去一样“装死”。各位可回想一下,2000 年刚好是 Intel 和 AMD 爆发 1GHz 时脉争夺战,并点燃后来长达 20 年 x86 双雄战役的关键时刻。产品时程表出现了 Centaur 史上第一个超纯量管线的 x86 处理器核心 C5X,与全新的 CX,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Nano。

C5X 不仅是货真价实的超纯量 x86 处理器核心,支援 SSE 指令集,更有着强大的动态分支预测、更深的指令管线与倍增的内部执行单元。当初 Centaur 没写在简报内的是,为了确保可每个时脉周期撷取两个指令,C5X 导入预先指令解码(Pre-Decode)的指令快取内存,提前标定快取内存内的指令边界(x86 指令集的长度并不固定),这让实际所需容量爆增 40%。

这很显然违背 Glenn Henry 的“信念”,也因此,预计 2001 年第三季出货的 C5X,真的能顺利诞生吗?预估的 55 mm² 看似不大,但你怎么猜得到威盛高层或 Glenn Henry 会吝啬到什么程度?更何况当“预算”超支的时候?

2001 年: 浮出调降电压、压低耗电量的 C5C“Ezra”。Cyrix 品牌也默默的消失。
Ezra-T 的那个 T 代表的是末代 Intel Pentium III“Tualatin”使用的改良版 P6 总线(Tualatin Bus,或称为 P3 Bus),AGTL 电压准位从 1.5V 调降到 1.25V,在还造成某些 Intel 芯片组的相容性问题,某些骨灰级电脑玩家应该依稀还有点印象。
C5M 仅用来进行样品测试,真正投入量产的是 C5N。
C5X 则延后到 2002 年,还跑出来衍生款 C5XL 和 C5YL,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全新未来架构从 CX 改名成 CZA,意义不明。
C5XL(Nehemiah)是 C5X 的砍半版本,也是 Glenn Henry 最爱的“超级纯量”处理器,符合“简单、迅速、便宜”的大原则。这时公布的 C5X 也与一年前略有出入,至少指令管线深度被缩短了,芯片面积也增肥到 78 mm²,隐隐约约让人感受到这踩到了某个人心中的红线。
“证实 Centaur 对简单微架构的执著是正确的”的 C5XL,牺牲 10% 整数与 20% 多媒体效能,但减少了 30% 晶粒面积,利于提高时脉,降低耗电,而且 C5X“更贵更热”。
2002 年:既然有了便宜的 C5XL,做为“先导研究案”的 C5X 就没存在的必要了,Centaur 首款超纯量管线 x86 处理器,就此胎死腹中。
但 C5XL 并非一团糟,相较于 C5N,在相同制程,C5XL 的面积更小,时脉更高,支援 SSE 指令集。让人眼睛一亮的是,C5XL 具备了多处理器环境必备的先进可程式化中断控制器(APIC),这让 C5XL 可实作双处理器组态,但这张支票到了 C5XL 的下一版 C5P 才兑现。
C5XL 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:浮点运算不再只跑一半时脉,真是可喜可贺。
不过,以 C5XL 做为全新起点的演进图,却更让人感到一头雾水。一个 C5X 被腰斩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,谁敢保证产品时程表上的代号,有几个可以苟活?更何况,给客户看因“比晶体管更厉害的谋略”而随时大风吹的产品时程表,对经营事业与开发客户,真的妥当吗?
千万不要改改 roadmap 没什么大不了,对 Intel 和 AMD 来说,一旦爆发这种大事,一堆人都要准备去“找头路”了。
偏偏这又是不少台商甚少意识到的坏习惯,自己关起门来“精雕细琢,近乎苛求”是一回事,改来改去(搞不好还改上瘾了)的“Roadmap”往往是客户规划产品时的大灾难。“先当个简报王,等有客户被骗上钩再开案”确实是常见的业务开发技俩,但这招玩久了,只会让自己彻底信用破产。此类英勇事迹,在业界可谓班班可考。
全新未来微架构又从 CZA 改名成 CN,意义依旧不明。
再跑出来多出 SSE2 指令集、强化动态分支预测的 C5Z。第一时间先问:它活得下去吗?
那个看起来很像“试水温”的 C5Y(疑似系统总线换成 VIA V4 Bus)和 C5XP(C5XL 的低耗电版),似乎也很危险。那颗不存在的 C5XL/Z 的系统单芯片,就假装没看到好了。
2003 年:威盛开始以市场区隔细分品牌:VIA C3 入门桌机、Antaur 笔电、Eden 嵌入式应用,继续大混乱中。
这提到了之前没讲到的 C5XL 的硬件乱数产生器(RNG,Random Number Generator),看来威盛想从资讯安全应用发掘一些独特的利基点。
又跑出来 C5XL 的微幅改良版 C5P,在“例行公事”降低耗电、缩减面积、提升系统总线之外,扩增本来该在 C5XL 就给的双处理器组态(DP)、虚拟化(VME)、分页位址属性表(PAT)、硬件乱数产生器(RNG)、和硬件 AES 解密等。但对 Centaur 和 Glenn Henry,减少 10% 芯片面积才是重中之重,就为了“简单、迅速、便宜”。
双 C5P 处理器看起来很威,但是威盛有信心两颗打得过人家 Intel AMD 的一颗吗?
0.18µm 制程、支援 SSE2 的 C5Z 跑到哪里去了?这个硬件 SHA-1 密码杂凑算法的 C5I 又是从哪边跑出来的?
2004 年:由“幸存者”C5P 为出发点,重新开展的时程表。
但这时候威盛 x86 处理器的时程表,总算有了一贯的逻辑(尽管维持双重核心代号):从 Pentium III “Tualatin”总线移转到相容 Intel Socket 479 脚位,但电器信号改用自家规格以避免侵权,并在通讯协定层面稍做改进(如资料写入效率)的 VIA V4 Bus。
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留意到:C5P 的规格又被偷偷的小改了。
2004 年 5 月 18 日公开 C5J 产品代号、2004 年 9 月 17 日公布 VIA C7 品牌、到 2005 年 5 月 27 日产品上市,C5J 算是历经 4 年的集大成之作,从制程、时脉、快取、指令集、总线、资安硬件功能到多处理器,在每个环节都有重大的跃进。
靠着 IBM 的 0.09µm 制程,C5J 芯片竟然缩小到 31.7 mm²,仅为 WinChip 2(95 mm²)的三分之一,Glenn Henry 这个人与其领导的 Centaur 团队,对于压低成本的执念之深,让人感到恐怖。也许把产品“cost down”到看起来很玲珑精巧,就是他们工作成就感的来源。
“几乎 Tape Out”的 C5I(被 C5J 取代),和 C5Q(台积电 0.13µm)、C5R(台积电 0.11µm)与 C5W(IBM 0.09µm 改良版),也就默默消逝在简报的尽头。
走过风风雨雨的 4 年,这么多的 Centaur 产品代号,扣除早期的 C5A/B/C,仅 C5N、C5XL、C5P 和 C5J 撑到量产上市的那一天。
很巧的是,这段期间,也正是 Intel 以威盛未得其同意,擅自销售 Pentium 4 处理器相关芯片组为由,对其发动官司诉讼大战,并纠缠了近 3 年。这场法律战的影响,与是否就是产品开发计划东改西改的主因,外人就不得而知了。
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:威盛和 Centaur 对“降低成本”的坚定信仰,如同信奉宗教般的虔诚。天真的相信,只要东西做得够便宜,就一样会有人愿意买单,又偏偏是不少台湾企业(或许可加上某些美国人)的通病。
最终不得不与魔鬼进行交易
俗语说的好:出来混的,总是要还。多年来死守“成本至上”信条、坚决抗拒高效能处理器主流技术趋势的 Centaur,终究得面对效能竞争力远远不如对手的残酷现实(到了 2005 年,还没有超纯量管线,距离 Intel Pentium 已 12 年),64 位元的普及速度超乎众多 x86 处理器小厂的预期(Transmeta 对此应该很有感),更是需要尽快提供解决方案的重点项目。
在 2004 年 10 月 5 日,跟随着 C5J(VIA C7)一同曝光的“全新下一代微架构”CN,很明确的昭告天下:Centaur 还是得拥抱超纯量管线、“魔鬼的工作”非循序指令执行、预测执行(结合动态分支预测和非循序指令执行),以及 64 位元和更高效率的多媒体应用效能。当然,在任何可以想到的环节,也势必要有足够的进化,才有可能跟得上 x86 双雄的脚步──最起码拉近那巨大的差距。
令人感到好奇的是:“面面俱到”的 CN,其产品开发时程,还能够像过去的 Centaur 产品,一样的神速吗?还有办法在两年之内,也就是在 2006 年就推出产品吗?
笔者只知道:从公司创立以来,微处理器报导(Microprocessor Report)举办的活动,几乎无役不与的 Centuar 与其看板人物 Glenn Henry,从 2005 年到 2007 年,就再也没站上这些活动的演讲台了。
等待了整整 3 年,2008 年 1 月 23 日,威盛公开代号 Isaiah 的新世代 x86 处理器微架构,3 月开始大量提供样品给客户,5 月 29 日正式命名为 Nano(凌珑)处理器系列。其脚位与 C7 相容,因此厂商与客户可用较低的成本升级产品,也同步推出超低电压的低功耗版本。
再来就是一连串事件发生时间与我们越来越近的故事。
2009 年 11 月 3 日,从富士通 65nm 制程转进至台积电 40nm 制程的 Nano 3000 系列,开始支援 SSE4.1 指令集,并修正“残废”的第二个整数运算单元,使其可执行大多数整数运算指令。
2011 年 5 月 5 日,台积电 40nm 制程 Nano X2 迈进原生双核心。
2011 年第三季末,四核心(两颗双核心封装成单一芯片)正式出货。
2014 年夏季,台积电 28nm 制程、时脉 2GHz 的“Isaiah II”样品与测试数据曝光,支援 SSE4.2、AVX 与 AVX2 指令集。
但却也被人发现:在某些 SPEC CPU 的效能测试项目,编译程式时启动 AVX / AVX2 时,效能不增反减,推测跟实作 AVX / AVX2 的手段有关,很可能只是透过修正微码实现相容性,但处理器微架构层面却毫无任何配套措施(Intel 和 AMD 都为此下足功夫),无愧 Centaur 那套“简单、迅速、便宜”的最高指导原则。
有趣的是,那时有人注意到,威盛有份“疑似打造 x86 / ARM 混合架构处理器”的专利,也刚好是 AMD 刚宣布将融合 x86 与 ARM 的系统架构,并研发 K12 处理器的“简报王”时期,让人不联想到威盛想趁机跑去凑热闹的念头。最后,无论是AMD和威盛,这伟大的创举,从来就没有成真。
总之,各位可以回忆一下,在任何威盛推出新品的时间点,Intel 和 AMD 摆在市场上的是哪些产品,又是怎样的制程和规格,又是何等规模的性能与出货。然后威盛与 x86 双雄的差距,就这样越拉越远。基本上,说威盛早就看不到那两家的车尾灯,恐怕也不会有太多人会“胆敢”反对。
至于威盛这间公司为何从叱咤风云的台湾股王,走向极盛而衰,到近几年面临下市危机的惨况,在过去早已是无数财经媒体的封面故事,就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,也没有特别为此大书特书的必要了。笔者只记得十几年前,威盛某高层曾豪情万丈的公开喊话:在嵌入式应用的市场,没有 AMD 的份。
难道威盛和 Centaur 的 x86 处理器,除了低价位的嵌入式应用整合方案外(其实威盛握有的武器是很完备的),就没有其他的出路吗?2019 年 11 月 18 日的新闻稿,倒是提醒了世人,他们并未坐以待毙,寄望从人工智能的推论应用,找出一条生路,甚至还有机会从 5G 时代的多接取边缘运算平台(MEC),切入服务器市场。
目标“人工智能推论服务器”的 CHA
在 2019 年 11 月 18 日亮相的 CHA 系统单芯片,整合了 8 个 CNS 处理器核心、16MB 第三阶快取内存、4 通道 DDR4 内存控制器、44 Lane PCIe Gen3、Ncore 人工智能辅助处理器,并可双处理器组态,2020 年下半年量产,这是自从 Nano 之后,睽违超过十年的全新设计。CNS 采用台积电 16nm 制程,芯片面积是“破天荒”的 195 mm²,标准设计功耗不高于 85W。而此时此刻,Glenn Henry 则已经是半退休状态了。
Centaur 宣称 CNS 是“Intel Haswell”等级的微架构,从环状架构(Ring)处理器内部总线也看得出 Sandy Bridge 到 Broadwell 的影子(之后的 Skylake 就转向更有效率的 Mesh 总线),但 22nm 制程的 Haswell 却早在 2013 年 6 月 4 日就已出现,技术整整落后超过 6 年的 CNS,论处理器核心的效能,根本一点拼面都没有。若无让人眼睛一亮的新兵器,连能否打得过 Intel“瞄准 5G 基地台商机”的 24 核 Atom 处理器,都是天大的问号。
所以除了连 AMD Zen2 都尚未支援的 AVX-512 指令集(虽然内部拆成两个 256 位元运算微指令,实际效能有所疑虑),就是从 5 年前开始热门的“人工智能处理器”下手了。
CHA 的产品定位,很明显的锁定 5G 时代的边缘服务器,如 ETSI NFV 架构的多接取边缘运算(Multi-access Edge Computing,MEC),或工业物联网的网关(Gateway)。较“古老”的 16nm 制程,大概可提高 CHA 对恶劣运作环境的防御力。而根据“人工智能即将无所不在”的教条,这些应用或多或少用得到推论功能(像人脸辨识之类的)。威盛想踏入高获利的服务器市场,意图不言可喻,但 CHA 值多少价格,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由 Glenn Henry 亲自操刀的 Ncore 人工智能辅助处理器,芯片面积 34.4 mm²(恰巧是他非常熟悉的尺寸),采用超宽的 32768 位元 SIMD 架构,借由理论值 20TB/s 的 16MB SRAM 挹注充沛的内存带宽,当执行推论常用的 INT8 短整数时,拥有每秒 20 兆(20T/s)的最高运算能量。Ncore 亦可支援在深度学习开始普及的 Bfloat16 浮点数,但峰值效能会只剩下 INT8 三分之一。
这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,但这性能究竟如何,可以参考一下 Google 的第一代 TPU(2016 年):INT8 最高效能约 92T/s。换句话说,Ncore 连其四分之一都不到,大致上跟 Pascal 架构(2016 年)的 nVidia Tesla P4 相去无几(22T/s)。同场加映 Turing 架构(2018 年)的 nVidia Quadro RTX8000 是 261T/s,推论专用的 T4 则是 130T/s。
当然,你也可以认定这个 Ncore 是“免费附赠”的,效能单位成本与“效能 / 功耗比”,可能远优于现有市场上的其他方案,无需外挂运算加速卡也是显而易见的优势。但对于人工智能应用,因为“硬件制造商和软件开发者”之间的鸿沟实在太深(像 Google 这样自产自用 TPU,反而就没这样的困扰),意思就是这票技术先驱者做出来的硬件,不是不好用就是不合用,导致 5 年前吸引众多有志之士一窝蜂涌入的人工智能芯片热潮,正在急速退烧中。
威盛和 Centaur 是否能够提供满足软件开发者的完整解决方案,避免重蹈覆辙,犯下无数“先贤先烈”的过往错误,将决定压宝人工智能这个决定的成败,否则,CHA 将沦为“即不简单,更不迅速,只能便宜”的低价产品。
唯偏执狂得以幸存,但却不会带来成功
“唯偏执狂得以幸存”(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),是Intel创办人之一的安迪‧葛洛夫(Andy Grove)的传世名言,一语道尽他战战兢兢、戒慎恐惧经营 Intel 的心路历程。但我们也很清楚,Intel 之所以会如此成功,也不是只靠偏执而已。Centaur 偏执于“简单、迅速、便宜”的理想之路,却是另一个极端的反例。
他们的确靠着死守着最低成本的坚持,成为 Intel AMD 之外,唯二还念得出名号的 x86 处理器厂商(另一间是俄罗斯的 Elbrus),但这些产品是否带来商业上的成功,相信各位心中自有定见。也许威盛并未供给 Centaur 足够的经费和人员,也施加极度严苛的成本要求,在 Time To Market 的前提下,难以完成更先进产品的开发。
这些年来,Centaur 也很可能存活得很艰辛,朝不保夕,个中甘苦,不足外人道也。但不幸的是,市场和消费者并不会理会这些“借口”,他们只会在意产品能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。
不计代价的把东西做到价格最低廉,就绝对会有人乐意接受?这世界的运作,从来就不是这么的简单,没有永恒不变、放诸四海而阶皆准的准则。或许,这就是坚守“简单、迅速、便宜”的 Centaur 和威盛 x86 处理器发展史,带给我们的教训。
(首图来源:VIA Gallery / CC BY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