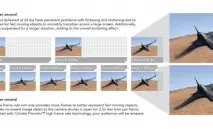武打巨星李小龙的名言,Be water,贯穿这场香港反送中运动。群众如水一般,无所不在,来去自如。
即便历时超过百日(第一场反送中游行在 3 月底),8 月 18 日,整日滂沱大雨,仍有 170 万人上街。港人真的如水一般,双脚泡在雨水里,从维多利亚公园流向铜锣湾、流向湾仔,再往金钟方向满去。
这场运动,没有明确领导组织、无人可代表群体发言,群众更反对“大台”(香港话指领导人、组织)。即便如知名港星何韵诗、雨伞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之锋等人,此次经常公开发言,都拒称自己是“大台”。
参与者不是听谁的一声令下来行动,而是利用新科技工具与网络平台,彼此号召、分工。“我们只有一个大台,就是(香港特首)林郑月娥,”8 月 16 日,学界反送中晚会现场,17 岁的香港少女琦琦说得义愤填膺。
但,一场参与者动辄破百万人的群众运动,没有系统性的物流、人流,甚至金流系统,却能持续数月,可能吗?
“怎么发展出可以运作的状况?这个必须要参与其中才能体会,但每个人也都只看到一部分而已,”香港议员朱凯迪坦言,身处其中的他,仍只看懂一部分。
每天 4、5 组人在台带货 百万装备,靠匿名者进香港
我们在台北水源路、环河南路一带的“五金街”,发现其中“一小部分”,开始追踪。
台北的五金街,在过去几周内,成了反送中物资供货点。当香港境内因持续抗争,口罩、护目镜、滤毒面罩开始短缺,港人转而直接或间接透过台湾朋友来此“带货”。
随意踏进太原路上一家五金店,不需开口,光用手比出面罩动作,店家就一目了然:“要防毒面具?去里面找那个小姐,她会帮你处理。”
店家们已习惯,一天内有 4、5 组香港或台湾客,来买平时只在工地使用的护具配备。有人一开口就要 5、60 套,几乎等同店家半年、一年内的进货量。“我哪来这么多货,一次才叫十几组!”一家太原路五金行老板娘摇头说。
因为需求太大,采买者甚至找上经销商大量采购。当“监工十多年的作家林立青,对工地配备熟门熟路,偶然受香港朋友之托,从一次代订 3、5 组,到如今一次购买几十万的货,意外成了台湾最大物资供给站之一。
就在 818 大游行前夕,台湾有团体与个人已搜集金额近百万元的“装备”打算送到香港前线。但林立青透露,他与朋友只负责代购,如何把物资运送到香港,又换另一群连他也不认识的“匿名者”接手。
救护站、黑警在哪全都露 加密软件让人人都变收发站
台湾五金店,不过是这整个无大台运作系统中的“冰山一角”。
走在香港游行现场,随处可看到街边转角,有人摆起“爱国五金”物资站;有人穿着黑衣、搬著瓶装水,就从大楼窜出。游行队伍里,群众总知道哪里有救护站,哪个地铁站、公车线暂不开放;甚至,他们知道何时有警察或黑警嫌疑人出没,较危险、须避开。
原来,他们手机里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中,有各种群组推播即时讯息。还有人利用 Google Map 做出外挂的“抗争地图”,由匿名者提供所在地各种资讯;当有人发出冲突警示、物资需求等,就有人在 Telegram 上发出载运物资、送人返家的资讯,有意者自行前往集合。
Telegram 让所有匿名参与者,在无组织、领袖情况下,人人成为讯息发送与接收站,自然的形成一个服务支持网络;同时,因为匿名,参与者更放心的贡献点子与发挥创意。
例如,为了举办今年 8 月初一场晚会,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崑阳,多次与知名连登仔(注:如台湾 BBS 站批踢踢)“我要揽炒”团队联系,但他从来“只闻其声不见其人”,不知道对方是谁。
但他毫不在意。“说实话,我不太需要知道他是谁,不知道就不知道,这很符合我们现在香港人的感觉:没有大台,大家不知道彼此身份的时候最安全,每个人才能发挥与贡献更多。”
然而,需要高度缜密计划的“勇武派”(指防护装备齐全、抗议手段较激烈的一群),也有一个较封闭的平台。
一位抗争者曾与《商周》记者分享一个制作精良的网络界面,上头是“勇武派”组织分工:除了抗争实况地图上标志警察、自己人、安全屋位置外,还有警车车号名单、前线与后勤如何任务分工。但当行动结束隔天,记者再打开该网页,整个界面已消失无踪。
“这些地图有时在重要时刻,才会出现,”张崑阳说,“这跟 be water 一样,一下出现,一下消失。”
如果 Telegram 是抗争者即时横向联系的工具,香港的连登,则是塑造运动论述、风向与沟通的大平台。
大平台“连登”包容性强 可快速修正运动、随时补位
“连登就像是‘公海’,把所有人聚集起来,人人可表达意见;香港 18 区,可能就有 18 个公海,里面上万上千人,依照各种不同主题再去分工,各自透过 Telegram 联系,”朱凯迪解释了连登与 Telegram 的不同功能。
他分析,连登原是较激进的平台,但这次却“比过去都包容”,“声音非常多元,以至让连登产生对运动快速修正的机制”。
例如,今年 7 月 1 日群众冲入立法会,是无计划性的行动,因此当下很需要有人解释行动意义;结果几小时内,连登就出现 3 篇占领立法会的宣言,同时产生如今反送中的 5 大诉求。“确实是有一些有想法的人先起头,但从想法到落实,不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,都要在连登上看群众支持度如何。”他说。 “运动是会不断犯错的,现场的人有时候会做过头,但马上会有人透过连登‘修正、补位’,连登就好像变成一个生命体自己发展,”朱凯迪认为,连登也有“性格”,如可能基本上较重视港人与国际讯息,忽略中国-的宣传论述等。
又如,在历经 8 月 13 日抗议者揍殴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记者的意外事件、中共官媒不断释放武警驻扎深圳恐吓影片后,连登讨论串也呼吁 818 游行走“和理非”(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)路线,让当天行动平和落幕,未爆发激烈镇压与流血冲突。
“没大台,起码在初期让中共很难掌握它(反送中运动),看不懂,只能说这是有外国势力在操控啊!”朱凯迪说,广东话有句俗谚“盲拳打死老师傅”,就是这种出其不意,让《送中条例》被挡下来。
中国与香港-看不清也不懂如何应对这种新抗争模式,部分港警甚至贬抑穿黑衣的抗争者,如昆虫一般,是杀不死的“曱甴(蟑螂)”。
“我们是杀不死的蟑螂!” 抗争者不受支配、集体分工
但其实,我们确实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懂这场运动如何运作:抗争者就像是一群蚂蚁或蜂群;运动 5 大诉求,则扮演蚁后或蜂王的角色,驱使蚁、蜂们持续追寻、动作。
蚂蚁或蜜蜂,被生物学家称为“社会性昆虫”,具有“真社会性( Eusociality)”。此概念由美国生物学家巴特拉(Suzanne Batra)提出,用以描述蜜蜂筑巢时互相合作、劳动分工犹如人类社会,甚至会保护弱小一代;蜜蜂们因为“想要达成某些事”,如采蜜、换巢,能在看似无人指挥情况下,做出协调一致的行动,形成一种无大台的集体支配。
如果把抗争者看作蜂群、蚁群,Telegram 就像是昆虫的费洛蒙和天线,借此串联沟通;虽然没大台,但大家却为了达成共同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、集体分工,甚至抵御天敌如警察,即便被“杀虫剂”如催泪弹喷杀,巢穴仍会持续孵化、持续繁衍。
在香港抗争现场,你经常会听见“揽炒”一词。
“就是抱着一起死,玉石俱焚的意思,”17 岁少女琦琦,在充满“我要揽炒”口号声的现场,对《商周》记者说,“当蟑螂也好,我们就是杀不死的蟑螂啊”。
这场动辄可集结逾百万港人的长期抗争,已在国际公民社会上,重重留下一笔。它是数位年代群众行动“O2O”(线上线下串联)一场最丰富的展演,但,别忘了能够驱动群众的,必是人性永恒的渴望,一如香港人这次搏的:民主自由。
(作者:管婺媛;本文由《商业周刊》授权转载)
延伸阅读:
- 杜奕瑾指小米 6 扳倒 Telegram?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科技攻防战